

你无法通过思考、逻辑分析和听道理来处理和应对情绪痛苦。如果个体的行为动机是通过“想太多”来避免“感受太多”,那么本质上,思考本身依然是一种认知与情感上的回避。
临床心理治疗中,常见的回避行为包括:
1. 频繁转移注意力(如工作狂或沉迷游戏娱乐);
2. 物质依赖(如酒精、药物、毒品或暴饮暴食);
3. 社交退缩;
4. 强迫行为;
5. 情绪或思维的压抑;
6. 自我批评(以减少社会性排斥);
7. 正念练习(作为回避焦虑的一种方式);
8. 情感麻木与解离。
然而,我们可能会忽视“过度逻辑思考”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常见的认知与情感回避形式。下文主要探讨两种认知与情感回避形式:“思维反刍”与“担忧”对个体心理障碍造成的长期持续性负面影响。
01
概念
担忧是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的核心特征,被定义为一连串的思维链,聚焦于对未来尚未发生的威胁,或倾向于认为未解决的问题会引发灾难性后果「1」
类似地,反刍被认为是抑郁障碍(MDD)中的核心认知加工过程与情绪调节策略。反刍同样被定义为一连串的思维链及其伴随的负性情绪,但与担忧的区别在于,反刍的内容聚焦于过去的错误或失败「2」。
广泛性焦虑与抑郁之间具有高度共病性,而担忧与反刍也在概念上存在重叠;二者均被定义为重复性、持续性的负性思维形式,会维持负性情绪状态并加重心理病理症状。
02
担忧的回避功能
担忧本身是一种令人不适的情绪体验,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反复担忧,并且无意识地将担忧作为回避形式?
相比于恐惧,担忧并不会诱发显著的心理生理反应,而是一种相对更模糊、生理与心理唤起程度较低的广泛性情绪困扰。担忧是一种大脑中重复的消极自我对话,内容聚焦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消极事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但这一认知过程主要以头脑里的言语形式而非生动形象的意象进行,因此并不真正激活强烈的情绪体验。
Borkovec的理论认为,担忧让个体从更强烈的负面情绪和意象中转移注意力。因此,担忧的功能是为了回避那些比担忧本身更加痛苦和强烈的情绪痛苦。
一项针对502名被试的研究,将参与者分为过度担忧者(在过去至少六个月中,大多数日子里对两个或以上主题持续担忧)和普通担忧者(不符合上述标准)。
结果表明,担忧主要是一种以言语为主导的认知加工过程,其核心特征在于使用抽象、语言化的思维方式来回避更具象、更具情绪激发性的意象内容。
过度担忧者报告的“思维占比”显著高于普通担忧者。同时,过度担忧者报告的躯体症状(如心跳加快、出汗等)更少;头脑中诱发情绪的意象占比越低、言语思维越占主导,个体的生理激活水平反而越低「3」。

担忧通过以语言化思维为主的认知过程“钝化”了情绪意象所引发的强烈心理生理反应,形成一种通过语言性思维维持低水平情绪激活的认知情感回避策略。
这种机制虽在短期内具有“缓冲”作用,却阻断了个体对恐惧意象和情绪内容的体验,进而干扰了核心情绪痛苦加工与转化过程,也解释了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的慢性、持续性以及难治性担忧。
后期的另一项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担忧作为一种认知情感回避策略的理论依据。结果显示:与无担忧者相比,高担忧组在描述问题时使用的语言更抽象,且更少涉及情景意象。通过灾难化访谈进一步验证了该趋势:担忧程度(无担忧、低担忧、高担忧)越高,个体在表达问题时表现出的具象性和意象性评分越低。

这些结果表明(见上图),担忧通过语言化、抽象化的思维,实质上是在回避情绪意象的激活所引发的更高水平的情绪痛苦和躯体化反应,进一步印证了担忧作为认知—情感回避机制的理论模型「4」。
通俗地说,担忧就像用话语的“雾”遮住了情绪的“实景画面”,个体通过反复用语言性的思维,如内心反复消极性的内部对话或抽象地认知分析,来避免接触那些像恐怖电影一样令人不安的画面和情绪反应。
03
担忧与创伤
许多GAD患者报告有创伤性经历的历史。

一项来自巴西的研究样本共26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72岁左右。结果显示,童年被虐待经历可能是GAD的重要早期风险因素之一。老年群体中广泛性焦虑的患病率为20.6%(n = 52),其中29%的个体报告曾在童年遭受过虐待。
广泛性焦虑组在身体虐待与焦虑型依恋维度上得分显著更高。此外,广泛性焦虑组在神经质维度得分更高,而在外向性维度得分更低「5」。

在一项对800名年龄介于11至17岁的青少年开展的为期两年的前瞻性研究中,研究者系统考察了不同频率的亲子虐待行为(分别为几乎没有、偶尔发生与频繁发生)与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症状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在几乎无虐待的情况下,无论父母教育背景如何,青少年的GAD发生风险均处于基线水平;然而一旦进入“偶尔虐待”范畴,风险便开始随父母教育程度的降低而显著上升——当父母皆未受教育时,其子女患GAD的风险已上升至基线的1.71倍;而在“频繁虐待”情境下,风险急剧攀升至7.31倍,远高于父母皆受教育家庭所对应的1.89倍「6」。
由此可推测,焦虑障碍个体所表现出的慢性担忧,很可能在功能上具有一种继发性调节作用,旨在分散对早期创伤性经历所引发的情绪痛苦的注意力。
同时,也有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患者在识别和命名自己的情绪上存在困难,也难以调节自己的负性情绪,比正常群体表现出对情绪的恐惧以及更明显的回避强烈情绪体验的倾向「7」。
04
对比回避模型
担忧与反刍的对比回避模型(Contrast Avoidance Model)
思维反刍与担忧这两种认知过程具有相似的功能,即作为一种调节情绪的尝试,其目的在于回避情绪反差(emotion contrast avoidance)。
个体之所以持续担忧,是为了避免经历从“平静状态”到“突然强烈负面情绪状态”的情绪反差。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核心情绪痛苦的回避,两者都通过维持一种慢性负性情绪激活状态,来避免更剧烈、突发的情绪落差。
这一理论模型的重点在于,担忧作为一种无效的情绪调节策略,旨在避免情绪的剧烈波动,尤其是从平静到痛苦情绪的急剧变化;患者通过担忧,防止糟糕事件诱发的情绪起伏。

项研究表明(见上图),担忧与反刍机制相似,通过预先适应负性情绪,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更强负性情绪冲击「8」。
一. 担忧作为情绪调节策略
广泛性焦虑障碍(GAD)患者敏感于情绪的快速变化,尤其是情绪从积极或平静状态突然转变为痛苦状态(情绪对比效应)。这种情绪的波动令GAD患者无法耐受。
为避免这种情绪波动,通过持续担忧,患者能够降低情绪从平静到痛苦的变化带来的冲击。这种慢性担忧使情绪波动幅度被有效压缩。当面临新的应激时,担忧作为“情绪缓冲”,已经处于慢性担忧状态的个体相较于中性情绪或放松状态个体,其情绪和生理反应波动幅度更小。
例如,GAD患者通过担忧使自己持续处于中度水平负性情绪状态,从而在面对潜在压力事件时,情绪波动不会过于强烈(如突如其来的恐惧或悲伤)。
二. 心理测评
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后来的研究者开发了用于测量对比回避模型的问卷(问卷条目如下):

1. 我担忧是为了让情绪保持稳定,而不是让自己开心后再经历情绪的低落。
2. 我担忧是为了防止情绪突然发生波动。
3. 我担忧是因为觉得让自己感到快乐最终可能会让我变得更糟糕。
4. 我担忧是为了避免情绪突然恶化。
5. 因为坏事可能随时发生,我会觉得担忧更让我感到安心。
6. 当我在担忧时,我感觉自己能更好地控制情绪。
7. 与其感到开心后再被突如其来的负面事件打击,不如直接担忧更好。
8. 当我担忧时,我感觉情绪上不会那么脆弱。
9. 我担忧是为了掌控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让外界事件左右我的情绪起伏。
10. 当我担忧时,我觉得自己比放松时更能掌控局面。
11. 如果我担忧,我就能在需要时保持情绪上的警惕和准备。
12. 我宁愿选择担忧,而不是盲目乐观,因为我知道任何时候负面事件都可能摧毁我的快乐。
13. 当我担忧时,我能够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14. 我倾向于担忧,因为当我感到快乐时,我总觉得像是在等待“坏事情”降临。
这项研究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揭示了担忧背后的三个核心动机「9」:
A、Worry to Avoid Negative Emotional Shifts | 担忧以避免负性情绪波动:通过担忧维持情绪稳定、避免突然的情绪跌落;
B、Worry Creates and Sustains Negative Emotion | 担忧带来并维持负性情绪:担忧会强化焦虑、紧张与痛苦感受,尽管个体出于“避免更大痛苦”的目的而担忧,但结果却是情绪进一步恶化;
C、Worry to Create Positive Contrast | 担忧制造积极对比:一种“认知性自我安慰机制”:个体认为如果预先担忧,最终事情顺利的话,会带来更强烈的正向情绪对比。
三. 担忧被强化
担忧的维持既受到正强化,也受到负强化的驱动。
正强化:情绪的积极对比
当担忧事件未发生(如预期中的糟糕结果未出现)或正面事件发生时(如超出预期的好结果),个体会感受到情绪上的积极对比。例如,持续担忧让个体对“最坏结果”做好心理准备,因此当事情没有像预期那样糟糕时,情绪上的改善更加显著(情绪对比)。
负强化:减少负性情绪对比
担忧通过减少从平静到痛苦情绪的剧烈波动而获得负强化:通过维持慢性/持续性的消极情绪状态,担忧让个体避免经历情绪上的突然冲击,从平静状态突然转变为惊吓、失望或痛苦。慢性担忧提供一种短期的情绪稳定,通过预先适应负性情绪,个体试图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负性情绪冲击。
对比回避模型强调,担忧在广泛性焦虑障碍中的核心作用是通过减少情绪波动(特别是从平静到痛苦的剧烈转变)来维持情绪稳定。这一机制使得担忧行为受到正强化和负强化。担忧短期似乎具有功能性价值,但长期维持了GAD的核心症状“担忧”的持续。
05
反刍的回避机制
反刍是一种被动地聚焦于自身痛苦症状及其可能原因和后果的心理过程。个体反复思考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引发的情绪体验,但这一过程并不会引发积极的反思,也不是以实际的问题解决为导向的思维加工过程。
个体会持续且反复地思考自己感受有多糟(例如:“我太伤心了”“我毫无动力”),以及关于这些情绪的原因和后果(例如:“我能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吗?”)。这类反刍性思维会导致负性情绪的加剧,并显著提高由抑郁情绪发展为抑郁障碍的可能性。
在哀伤研究领域中,反刍是一种对“丧失”诱发的高强度情绪体验的认知性回避,与情感否认和思维压抑一样,都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而这些认知与情感的回避在维持或强化复杂性、慢性或延长性哀伤及其相关的共病障碍(抑郁、PTSD)中起着关键作用「10」。
Eisma 等人(2013)发现,反刍常以抽象、语言化的思维形式持续出现,这种“非意象”的认知可能有助于抑制更具情绪冲击性的丧失有关的情境或形象生动的记忆,例如死亡瞬间、临终场景或与逝去亲人的情感连结的点滴记忆。这种抽象语言形式通过剥离具象的情绪触发trigger,降低了情绪激活水平,从而暂时缓解痛苦体验。

从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见上图)和中介模型来看,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反刍 → 回避 → 情绪困扰”的路径。具体而言,悲伤反刍不仅与复杂性哀伤和抑郁症状显著正相关,还与多种回避策略呈中度以上正相关,包括经验性回避、思维压抑与行为回避等。
进一步的中介分析结果表明,悲伤反刍对复杂性哀伤的预测效应显著通过“经验性回避”间接传递。个体在经历丧失后,因恐惧直接面对“丧失却不可逆转”的现实所引发的强烈情绪(如情绪的崩溃、失控)倾向于回避自身的内部情绪体验,在认知层面,即通过反复咀嚼一些相对安全、概括抽象性的问题,来代替更直接地面对和体验丧失带来的情感冲击。因此,反刍阻碍个体对丧失事实的情感转化与意义整合,维持并加重了复杂性或延长性哀伤「11」。
另一项研究聚焦于重复性消极思维(repetitive negative thinking)尤其是反刍与担忧在丧亲个体心理障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共招募了474名近期丧亲的成年人(82%为女性),评估了个体的反刍水平、担忧、丧失相关回避、行为回避,以及抑郁症状与延长性哀伤症状的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认为(见上图),反刍或担忧并不仅是直接导致延长性哀伤或抑郁的因素,而会通过激活两种回避策略(行为回避和认知回避)间接造成抑郁与延长性哀伤症状的持续。

反刍和担忧二者均与延长性哀伤症状以及抑郁症状均呈显著中等正相关,反映二者作为持续性与反复性的消极思维模式对丧亲后的适应造成干扰。
此外,两类回避策略均与负性情绪反应高度相关。一类是失落相关回避,即对与死亡相关的痛苦记忆的认知回避,个体出于恐惧而不愿触碰“失去已成事实”的现实;另一类是行为回避,即丧亲后对日常活动的逃避,通常是由于丧失带来的情感麻木或生活意义的瓦解。其中,行为回避与抑郁和延长性哀伤均呈现出最强的相关性「12」。
06
总结
反刍和担忧看起来像是在进行逻辑的思考和分析,但其实往往是一种“用想代替感”的认知与情感的回避策略。人们习惯性地通过不断地逻辑分析来避免直面内心深处的核心情绪痛苦,比如哀伤、羞耻、恐惧或孤独。
这种策略背后常常受到一种积极元信念的驱动,例如“只要我通过持续的逻辑分析,将问题想清楚搞明白,就能避免最坏的结果或解决情绪痛苦”。而,现实的情况是:
你无法通过逻辑的分析与思考绕过人生经历中无法规避的核心情绪痛苦,
The only way out is through.
往期推荐
如何更有效处理思维反刍|基于元认知ATT练习(附实操步骤)如何与焦虑和担忧共处|精选汇总 Merry Christmas如何有效区分情绪|直达核心情绪痛苦强迫障碍患者情绪痛苦不耐受|治疗经验分享
作者:WYPSY工作室
中文原创 禁止转载,截取和二次加工 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Borkovec, T. D., Robinson, E., Pruzinsky, T., & DePree, J. A. (1983).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worry: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cess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1(1), 9–16. 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83)90121-3Nolen-Hoeksema, S. (1998). Ruminative coping with depression. In J. Heckhausen & C. S. Dweck (Eds.),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pp. 237–25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27869.011
Freeston, M.H., Dugas, M.J. & Ladouceur, R. Thoughts, images, worry, and anxiety. CognTher Res20, 265–273 (1996). https://doi.org/10.1007/BF02229237
Stoeber, J. (2000). Worry, thoughts, and images: A new conceptualization. In Generative mental processes and cognitive resources: Integrative research on adaptation and control (pp. 223-244).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Santos, M. A., Jardim, G. B., Ranjbar, S., Gholam, M., Schuster, J. P., Gomes, I., & von Gunten, A. (2023).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late-lif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re personality and attachment characteristics mediator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Reports, 12, 100514.
Lakhdir, M.P.A., Peerwani, G., Soomar, S.M. et al.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to-child-Maltreatment and self-reporte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ymptoms in Pakistani Adolescents.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Ment Health15, 36 (2021). https://doi.org/10.1186/s13034-021-00387-1
Olatunji, B. O., Moretz, M. W., & Zlomke, K. R. (2010). Linking cognitive avoidance and GAD symptom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of emo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8(5), 435-441.
Jamil, N., & Llera, S. J. (2021). A Transdiagnostic Application of the Contrast-Avoidance Model: The Effects of Worry and Rumination in a Personal-Failure Paradigm.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9(5), 836-849. https://doi.org/10.1177/216770262199179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21)
Llera, S. J., & Newman, M. G. (201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wo measures of emotional contrast avoidance: The contrast avoidance questionnaire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49, 114–127. https://doi.org/10.1016/j.janxdis.2017.04.008
Stroebe, M., Boelen, P. A., van den Hout, M., Stroebe, W., Salemink, E., & van den Bout, J. (2007). Ruminative coping as avoidance: a reinterpretation of its function in adjustment to bereavement. European archives of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257(8), 462–472. https://doi.org/10.1007/s00406-007-0746-y
Eisma, M. C., Stroebe, M. S., Schut, H. A., Stroebe, W., Boelen, P. A., & van den Bout, J. (2013). Avoidance processe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symptoms of complicated grief and depression following los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22(4), 961–970. https://doi.org/10.1037/a0034051
Eisma, M. C., de Lang, T. A., & Boelen, P. A. (2020). How thinking hurts: Rumination, worry, and avoidance processes in adjustment to bereavement.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27(4), 548–558. https://doi.org/10.1002/cpp.2440
责任编辑:微青
用户在壹心理上发表的全部原创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回答、文章和评论),著作权均归用户本人所有。独家文章转载,请联系邮箱:content@xinli001.com
举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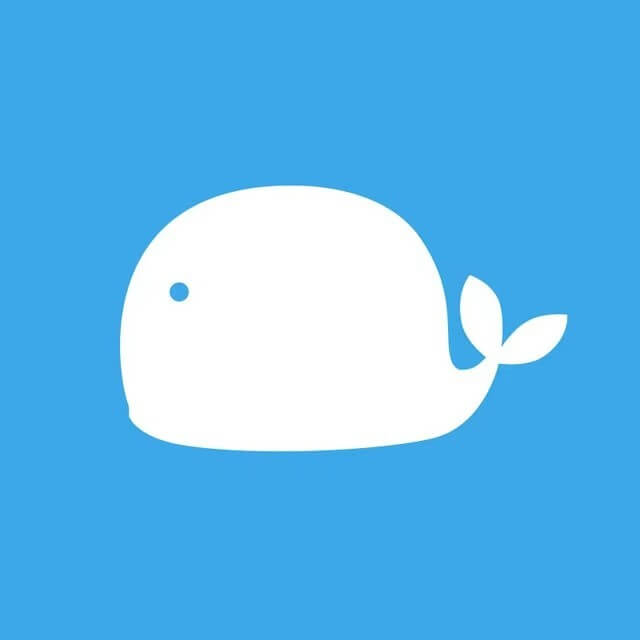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1691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1691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