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笔:商昔
编辑:商昔
责编:彭秋红
来源:微信公众号:沈家宏心理(ID:shenjiahongweixin)
01
增加伤害的善意
过去就没有抑郁症多动症这种东西,全是西方人发明出来害人的,都是他们提了之后中国人才得了这些病!
我相信,大部分对心理学有所了解的人,对这种言论只会报之一笑。
这种话也太荒谬了,难道在抑郁症发明之前,农村里就没有疯子吗?就没有郁郁寡欢的女人,没有精神失常的男人了?
这里有很明显的逻辑错误,即把一个之前没有命名的事物当成不存在。
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言论背后,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呢?
别急,先听我讲个故事。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对斯里兰卡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数十万人丧生,社区被摧毁。
随后,大量来自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涌入该地区,希望为幸存者提供心理援助。
这些来自西方心理专家,想当然地认为,全世界人对于灾难事件的心理反应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在遭遇海啸这种打击后,很快就会有上百万人遭受PTSD,所以当地人需要我们。
这些心理工作者会主动寻找幸存者,包括一些小孩,鼓励他们一遍遍地讲述海啸发生时的细节——如何失去亲人、如何挣扎求生、看到了怎样的惨状。
而许多孩子一开始根本不想谈这些,他们更想回学校。
那些治疗师认为,不愿意诉说的孩子“显然活在否认之中”,也就是他们采取了否认的防御机制。
然后,问题出现了。
幸存者们原本认为自己的悲伤、失眠、沉默是面对巨大灾难后的正常反应,但在心理工作者的干预下,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有缺陷的、不正常的。
按以往的数据,灾难后的PTSD患病率为15%-20%,这些患者中,又有16%的人会自杀。
而测量之后显示,他们的实际PTSD发病率为14%-39%。
相当于,接受了心理治疗的幸存者,反而病得更多更重了。
这个故事在伊桑·沃特斯的《像我们一样疯狂》有写。书中还有更多的心理科普确实会增加创伤的例子。
可能有人会问:一定是心理概念普及导致的原因吗?不能是斯里兰卡人更加脆弱吗?
那么,我回答一下:在一个充满了自然灾害、几十年的内战、青年暴动、贫困交加的国家,大部分斯里兰卡人依然能保持日常的功能和积极的期盼,这样的民族的韧性会比其他民族弱吗?
显然,是干预导致了问题。
所以,这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让受伤者认识到他所遭遇的可以称之为创伤事件之后,非但不能舒缓他的痛苦,反而加重了?

02
错位的文化解读
有一个概念可以回答:创伤的文化构建性。
这个词的含义是:痛苦是普世的,但我们如何体验、理解和表达痛苦,则是由我们所处的文化塑造的。
人类的痛苦体验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理过程,而是一个需要被文化和语言来塑造的过程。
没有文化的解读,我们的痛苦只是一片混乱而模糊的感受,在当人们感到痛苦和困惑时,文化会为他们提供一套可供选择的、被社会认可的痛苦表达方式。
举个例子的来说,西方对PTSD的认知逻辑是这样的:
1、命名:我得的是什么病?PTSD。
2、病因: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因为我亲历了海啸,我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和损伤,无法恢复正常。问题的核心在我头脑内部。
3、症状:我应该有什么感觉?我会有侵入性症状、回避症状、负面认知与情绪、高度警觉。
4、对策: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吃药。
好的,现在你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你感觉不再那么混乱了。
而在斯里兰卡,解读方式是这样的:
1、命名:我遭遇了什么?
一场巨大的不幸,一件我们必须集体去承受的命运。
2、病因:我为何如此痛苦?
因为我的社会被摧毁了。我的家人和邻居死了,我的渔船没了,我的房子塌了。
3、症状:我有什么感觉?
我感到痛苦,因为我不再是一个能够照顾孩子的父亲,不再是一个可以和邻居聊天的渔夫。
我的心中像有火在烧,我的头脑发热,我的关节和肌肉感到疼痛。
4、对策:我该怎么办?
我应该和还活着的人待在一起,和我的邻居们一起重建房子,修复渔网,清理废墟。通过共同的劳动来重建我们的社区。
我必须参加葬礼、社区的悼念仪式,来安抚逝者的灵魂,并与社群一起确认我们共同的悲伤和希望。我会去找僧侣,让他们帮助我理解这场不幸。
发生海啸的创伤,在斯里兰卡人看来,痛苦更多来自于人际关系。
我的亲人死了,我的朋友没了,我无法继续承担我在家族中原有的角色。正如《像我们一样疯狂》原文里所说:“海啸产生的破坏不是发生在头脑,而是在自我之外——在社会环境当中。”
看出来了吗?两种文化痛苦的因果逻辑是颠倒的。
西方逻辑里,内在的情绪问题(创伤)导致了外在的个人功能受损。
因为我很难过,我无法再继续承担一个爸爸的角色了。
痛苦源于内在情绪的失调,是内在的、个体化的和情绪中心的。
而在斯里兰卡的逻辑里,是外在的社会关系被破坏导致了内在的痛苦感受。
因为儿子死了,所以我无法再当爸爸,所以我很难过。
痛苦的根源是外部的、社会性的和关系性的。
西方咨询师试图通过谈话治疗来修复幸存者内在的恐惧和焦虑,他们相信只要解决了这些情绪问题,社会功能自然会恢复。
但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这种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
他们真正的痛苦根源是无法通过与一个陌生人谈论内心感受来修复的。你无法通过谈话重新获得一个逝去的儿子。在斯里兰卡人需要加强社会联系的时候,西方人却要求他们进行一场一对一的心理咨询。
这种做法不仅是无效的,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新的伤害。因为它强行用一套个体化和病理化的语言,去覆盖并否定了当地集体性和社会性的疗愈传统。
那么,这种创伤概念的强行挪用,是如何一步步将幸存者正常的悲伤,扭曲并固化为一种难以摆脱的创伤呢?

03
痛苦是如何加重的
首先,这套理论将痛苦病理化了。
在此之前,海啸带来的痛苦是正常的,人们会说“心中有火”或“头脑发热”,但他们并不将灾难后的痛苦视为一种需要个体化治疗的精神疾病。
相反,痛苦是一种集体体验,当整个社区都遭受重创时,个人的悲伤是正常且必然的。
而西方人在做的,恰恰是把他们的痛苦病理化。
一个孩子在海啸后害怕大海,拒绝下水,这是一个完全正常且理性的恐惧反应。但在PTSD的框架下,这种回避行为被记录为需要干预的症状。
它模糊了正常的恐惧和病理性的创伤之间的界限。
它让家长和孩子们都开始相信,他们的自然反应是一种病,从而产生了不必要的焦虑。
其次,它将人们的身份置换了。
在干预之前,人们的身份是“渔夫”、“母亲”、“邻居”,他们首先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
干预之后,许多人首先认为,“我是一个PTSD患者”。他们将注意力持续聚焦于自身的创伤症状上,强化了无助感。
真正对斯里兰卡人有效的解决方式已经在斯里兰卡的文化中——重新构建一个社会交际群体,重新回到社会关系中,那些说着“我想回学校”的小孩,已经在进行自我治疗。
因此,当西方干预者专注于治疗内在情绪时,反而因为其对真正痛苦根源的无视,而让幸存者感到更加的困惑与孤立。
最后,这一整套的理论会让人不自觉地靠近症状预期,并将其固化下来。
当一个人接受了自己患有PTSD的诊断后,他会开始预期自己应该有某些症状,比如对声音敏感、容易受惊。
这种预期会让他无意识地草木皆兵,从而使他真的处于一种高度警觉的状态。
这又反过来印证了他“我有PTSD”的信念。
我再说一个离我们更近的,香港的厌食症案例。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人对“厌食症”这个概念几乎闻所未闻。
西方厌食症患者的一个特质是“对肥胖恐惧”,但香港之前的厌食症患者之前并没有这种体验。
勉强的几例吃不下饭,疑似厌食症的案例,也没有表达出西方厌食症患者标志性的“对肥胖的恐惧”。
他们描述的仅仅是:肚子胀或喉咙堵塞。
他们不会刻意限制自己的饮食,只是单纯吃不下。
但在1994年,一个夏琳的女孩去世了,大量的媒体采用了西方的厌食症叙事来报道此事,几乎照抄了DSM里对厌食症的描述,例如病态减肥、害怕变胖之类的词。
于是,在10年不到的时间,厌食症的患病人数增长了25倍,并且,他们的表现和感受,变得与DSM里所描述的越发一致。
《像我们一样疯狂》中写道:“在教育全世界像我们一样思考的同时,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使这个世界‘发疯’的样子越来越相似。”
看到这里,可能已经有人对心理科普充满反感。
我们很容易会得出一个结论:心理学的全球化是一场善意引导的文化灾难,它增加了原本没有的创伤,让原本不存在的精神病人诞生了,它不应该存在。
但,这真的是故事的全貌吗?
对于那些在“抑郁症”这个词出现前,只能被家人和社会当成疯子、懒汉或想不开的人来说,这个来自西方的标签,究竟是束缚他们的新枷锁,还是一把让他们得以求助的钥匙?
斯里兰卡的案例揭示了强行挪用的危险,但如果我们因此就全盘否定,是否又会陷入另一种形式的无知?
心理学的科普,究竟多大程度上带来了创伤,又多大程度缓解了创伤?
下一期,我们会谈论这些问题。
作者简介:商昔,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沈家宏心理(ID:shenjiahongweixin),沈家宏心理致力于家庭系统动力学与个体心理的研究、运用与传播,打造一个集心理咨询、心理培训、心理督导、心理测量、心理网络产品、心理学物化产品、员工心理援助计划为一体的专业心理服务平台,旨在促进个人在家庭、学校、职场、婚姻中健康幸福的成长。

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对您有帮助,欢迎分享给更多的人,一起传播心理学知识,让世界更美好❤
原作者名: 商昔
转载来源: 微信公众号:沈家宏心理(ID:shenjiahongweixin)
转载原标题: 心理概念越科普,得精神疾病的人也越多
授权说明: 口头授权转载
用户在壹心理上发表的全部原创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回答、文章和评论),著作权均归用户本人所有。独家文章转载,请联系邮箱:content@xinli001.com
举报
作者未开启鲸币认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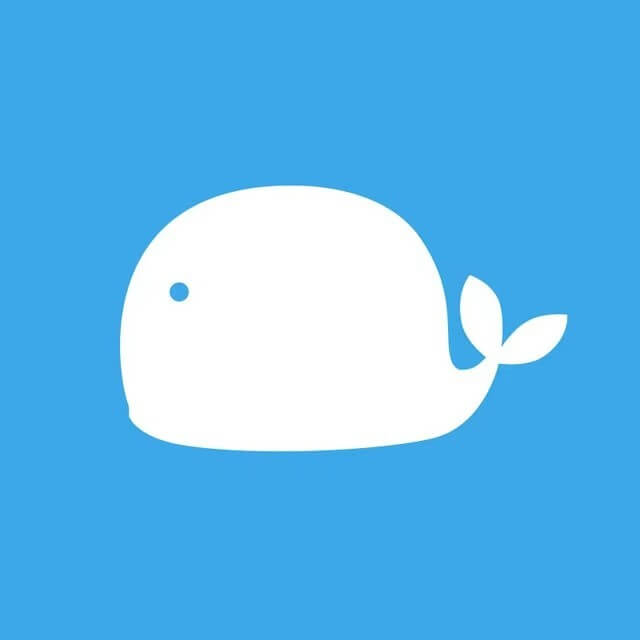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1691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1691
回复